

1986年4月26日清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在一次安全测试中,能量水平骤降,操作员撤出了大部分控制棒,试图使反应堆恢复运行。它开始过热。科学家们希望能中和系统,将控制棒推回,但他们不知道,这些控制棒的顶端是石墨,一种助燃剂。砰。
如果你整个夏天都提心吊胆地盯着HBO的《切尔诺贝利》,那么这已经是旧闻了。这部备受赞誉的电视剧 为了叙事而牺牲了不少事实,不应被误认为是纪录片。但创作者们却精心将他们的五集迷你剧编织进了文化和科学细节之中:《纽约客》的Masha Gessen称,布景“以西方电视或电影——乃至俄罗斯电视或电影——前所未有的准确度再现。” 最后一集以一个法庭场景为主,其中三个角色详细解释了事故的细节,包括石墨。在连续五集令人痛苦的观看体验中,该剧始终致力于真实感,而非事实本身。
这使其有别于近七十五年来许多描绘核能的叙事,那些叙事曾以关于核变异者的奇幻故事激发公众的想象。但我们已经了解到,核灾难的真实后果可能同样可怕。

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了两颗原子弹。但仔细的 审查制度 意味着美国人对细节知之甚少,尤其是关于辐射及其影响。这意味着公众情绪是复杂且常常自相矛盾的。Cyndy Hendershot,阿肯色州立大学英语教授、冷战流行文化专家表示,对许多人来说,“原子弹被视为性感”。他们随着“Atomic Baby”之类的摇滚歌曲起舞,并穿着以比基尼环礁命名的泳衣,那里是美国重要的核武器试验场。
然而,对核末日日益增长的焦虑需要一个宣泄口,好莱坞的怪兽电影提供了这一点。Hendershot说:“有一些严肃的剧情片讲述了核战争的真实情况,但人们不想看那些。”相反,他们转向了B级电影——低成本、高戏剧性的作品——以一种迂回的方式看待灾难。正如Susan Sontag在她1965年的里程碑式文章“灾难的想象”中所说,这些电影让观众“参与到亲历自己死亡,甚至城市死亡、人类本身毁灭的幻想中。”你带着恐惧走进影院,却可能带着笑声出来。
Hendershot说:“最初的变异者很可笑。” 1957年,《惊天动地一万米》和《不可思议的缩小人》在几个月内相继上映。两部电影都讲述了普通人暴露于核辐射后,产生灾难性且截然相反的影响。那个身高五十英尺且还在不断长高的男人恐吓着周围的人。Hendershot说,他因变形而心理崩溃,穿着“像尿布一样的东西”摧毁了拉斯维加斯。最终被军队击毙。而缩小的男人则任由周围的各种生物摆布。他被家猫咬伤,在用一枚安全针与蜘蛛搏斗后倒下。但他以精神健全的状态结束了电影:他很快就会被分解成原子,但他在意识到万物都是由微小粒子构成时找到了平静。

Hendershot说,在这些以及其他美国电影中,变异者受到了糟糕的对待。他们可能是原子试验的受害者,但在更广泛的世界里,他们本身就是威胁。这确保了每部电影都有“迪士尼式的结局”,正如汉德里克斯学院院长、日本学家Bill Tsutsui所称。如果只有一个危险的个体(或者,在Tsutsui最喜欢的子类型,“巨型蚂蚁电影”中,只有一个变异的蚂蚁群落),军队就可以控制威胁,保护社会安全。相比之下,由亲身经历过核灾难的人制作并为他们拍摄的日本电影,对变异者更为同情。而且它允许个人和政治伦理困境不解决。
导演本多猪四郎于1954年发行了第一部《哥斯拉》电影。(在日本,这个怪物被称为“Gojira”,是“大猩猩”和“鲸鱼”的组合。)这部电影是在当年“第五福龙丸”事件后制作的,美国在比基尼环礁的一次氢弹试验污染了一艘日本渔船。影片讲述了一个古老的怪物被太平洋上的氢弹试验唤醒的故事。一位受人尊敬的动物学家在影片的大部分时间里都在为哥斯拉的生存权辩护,但最终为了人类的利益而帮助消灭了它。一位创造了邪恶的“氧气破坏者”——这是唯一能够击败怪物的武器——的科学家销毁了他的笔记,并和哥斯拉一起溺亡,以防任何人能够重现他的作品。尽管他们做出了牺牲,但影片结尾,角色们得出结论,只要武器试验继续,“另一个哥斯拉就有可能在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再次出现。”这既是为续集(现在已有34部)做的完美铺垫,也是对核不扩散的真诚呼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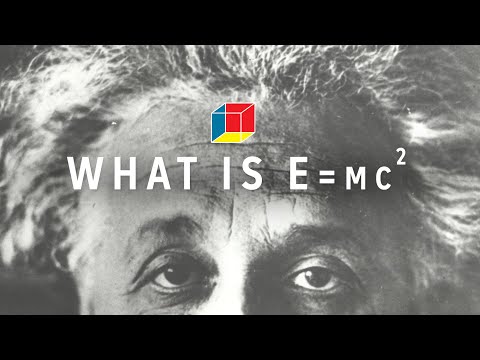
Sontag在“灾难的想象”中写道:“科幻电影中绝对没有任何社会批评,即使是最含蓄的批评。” 十年后,这种不考虑背景的故事讲述变得越来越不可能,即使在美国。1979年,宾夕法尼亚州的三哩岛发电站发生部分熔毁。1965年至1982年间,支持美国对日本投核弹决定的美国人比例下降了7个百分点,降至63%。那一年,一百万人聚集在纽约市中央公园,抗议原子武器,这是当时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抗议活动。
社会批评无处不在,包括银幕上。随着冷战的进展,核武器和核电站从科幻领域走向政治惊悚片,从B级电影走向奥斯卡获奖影片。两部备受好评的电影,《中国综合征》(1979年上映)和《丝伍德》(1983年上映),都聚焦于决心揭露发电设施掩盖真相的普通美国人。

HBO的《切尔诺贝利》在很多方面,是这种叙事基因的现代变异。下属反抗上司但失败了。同事们撒谎、欺骗,争夺利益。这是一种标准的职场纪实虚构——一个被辐射毒害的《办公室》。当核变异者确实出现时,他们的存在是含蓄的,至少与一个穿着巨大尿布的50英尺高的男人相比是如此。第一集结尾,一只濒死的鸟掉在人行道上。这只“煤矿里的金丝雀”剧烈抽搐着,而当地居民却浑然不知,还在附近不以为然地忙碌着,他们不知道附近发电厂正排放着危险物质。后来,剧集描绘了一队“清理员”,他们的任务是在“隔离区”(爆炸反应堆周围的限制区域)内杀死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动物。他们的目标?防止野生的、流浪的以及宠物动物将辐射带到它们的皮毛里。
如今,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已从最初围绕核电站的19英里半径扩大到横跨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1600平方英里 的区域。尽管污染将持续数千年,但各种生物,从鸟类到人类,仍然生活在隔离区内,并且至关重要的是,也在里面进食。居民面临的风险是真实的。虽然在没有大型人类聚居区的情况下 野生动物正在蓬勃发展,但 燕子 长着白化斑纹的羽毛;因食用受污染的蘑菇而带有放射性的野猪,从 瑞典 漫游到 捷克共和国;科学家们担心居住在该区域的欧洲灰狼可能会将其 突变传播 到整个大陆的种群。
至于人类,该区域内或周围人群罹患某些疾病的风险似乎有所增加。将辐射暴露与公众健康结果之间建立严格的联系几乎是不可能的,研究结果也常常有争议,但有研究 将 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以及饮食、酒精和年龄等其他因素)与受影响地区妇女的流产风险增加 联系起来。研究还 将 白俄罗斯受污染的牛奶与儿童甲状腺癌风险增加 联系起来。

MIT科学、技术与社会学教授Kate Brown说,对于少数能负担得起清除当地土壤污染物或运入新泥土的富裕人群来说,在受污染地区安全地种植食物是可能的。看看Atomik Vodka就知道了:本月早些时候,一组科学家 宣布 他们成功地将生长在隔离区的谷物蒸馏成一种安全的饮品。但土壤修复的技术复杂性并不是伏特加成为病毒式网络轰动的原因。是Мы对隔离区的痴迷——那个被人类傲慢所毁、在我们缺席中重生的最禁忌的地方。
自乌克兰 在2010年开放 切尔诺贝利地区旅游以来,已有数千人参加了国家批准的对被遗弃城镇、被大自然重塑的废墟,甚至核电站本身的游览。他们的经历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包括Instagram。声称该地区是社交媒体影响者目的地 的说法被大大夸大 了;隔离区当然还没有取代巴厘岛的海滩。但这可能会改变,因为乌克兰总统沃洛德米尔·泽连斯基(他的资历包括曾扮演乌克兰总统)决心 重塑 他国家的“品牌”。他说,这首先要让切尔诺贝利成为一种不同的热点。
尽管允许的旅游大巴众多,但非法进入该地区的行为仍然存在。一群受第一人称射击游戏启发的“潜行者”一次又一次地进入该区域。Brown说,大多数似乎是年轻人,他们像丹尼尔·布恩一样被边疆所吸引,决心考验自己的胆量。他们随身携带盖革计数器——不是为了避免辐射,而是为了寻找辐射。有些人喝那里的水, 吃 树上的苹果。
潜行者将隔离区的探索推向了极端,但他们的动机可能与那些合法探险的Instagram用户相同。Brown推测,许多人被切尔诺贝利吸引,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历史,更是因为他们觉得它可能代表着未来:“当我们担心气候变化和地球的宜居性时,我可以看到人们产生那些恐惧,”她说。“当我们有恐惧时,我们会做什么?我们会看恐怖片”——或者进行惊险的旅行——“然后吓唬自己,这样我们的焦虑就会减轻。”
原子时代的开端至今已有七十四年,核变异者依然存在。他们在市场上面临着激烈的竞争,来自关于更现代恐惧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比如 病毒爆发和恐怖主义。随着对核战争的恐惧减退,气候变化的现实逐渐显现,20世纪50年代那种戏谑式的恐怖早已被缓慢死亡的动物和衰败的景观所取代。它们也不再是随机事件或无辜事故的结果,而是深刻的人类错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我们的怪物,如果我们愿意倾听,它们有话要告诉我们。
